剛下火車,撞入眼簾的是月台上的造型裝置、純藍的天、無垠的田,幾名背包旅客走過,是為了過兩天的雲門舞集演出。這裡是池上,在人稱的「後山」。
已駐村4年的蔣勳說:「池上教會了我兩件事,一個是自然秩序、一個是土地倫理。」已在都會佚失的人情與自然、古早美食,這裡都還在,「到池上,我最大的領悟就是『天長地久』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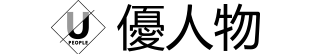
剛下火車,撞入眼簾的是月台上的造型裝置、純藍的天、無垠的田,幾名背包旅客走過,是為了過兩天的雲門舞集演出。這裡是池上,在人稱的「後山」。
已駐村4年的蔣勳說:「池上教會了我兩件事,一個是自然秩序、一個是土地倫理。」已在都會佚失的人情與自然、古早美食,這裡都還在,「到池上,我最大的領悟就是『天長地久』。」
蔣勳2014年秋天應「台灣好基金會」之邀,成為首批池上駐村藝術家,一年有大半時間在此,感受池上的魅力,而這魅力來自緩慢卻生氣勃勃的生活。
池上國中老師的舊宿舍被改為駐村時的「家」。綠色塗漆的木窗,夜晚被風一吹會「共共」作響,後來入住的年輕藝術家不明所以,蔣勳卻是「沒有那個聲音好像會睡不著,因為那是童年的聲音記憶」;陽光灑落在白牆上,幾條黑色電線大刺刺破壞那片白,帶動了天花板上的電扇或日光燈。
院子出去轉個彎,舊宿舍浴室變成畫室。不大的空間,光線挾自然風貫入,以紗門隔絕的後院,草木蔓生,一棵大樹甚至穿破水泥地。蚊子讓台北客逃之夭夭,畫家卻仰著頭兀自欣賞樹葉、屋簷、天空的平衡之美。
「來到池上,我對日出日落、春分秋分有了新的感覺,什麼時候插秧、什麼時候花要交配、人的身體會有什麼改變,這些都會有所感應。」蔣勳說:「我找回了自然秩序,重新跟著這個秩序生活。」
例如,春分過後,天氣轉暖,鄰居的耕耘機4點多就發動熱引擎,在農人5點下田時,蔣勳也起床了。到旁邊小店買現打的五穀漿跟高麗菜包當早餐,然後往東走、再往南,左手邊就是海岸山脈、右手邊就是中央山脈,大概5點45分日出,「太陽完全像個spotlight打在中央山脈,那個時候最漂亮。」
蔣勳走完一萬步,就回到畫室畫畫,直到黃昏時再次出門,此時已是燦爛晚霞打在海岸山脈,「每天晨昏兩次看到的山,一次是中央山脈、一次海岸山脈,被太陽照射著。我們常太依賴人為的照明,忘記太陽本身的照明迷人的不得了。」
在池上的一天到晚上八點,街上已沒什麼人,蔣勳上床看看書就入睡,「在這裡,很自然就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」
「小時候為了省電,吃完晚飯大概都在院子裡,媽媽會講『白蛇傳』、『封神榜』,只有星光跟月光。而那個感覺,現在也只有池上感覺得到了。」池上為了稻米好,100多家農民聯署拆掉了「天堂路」的路燈,把池上的天幕留給星月。
蔣勳常常一早開門,發現門口有人放了油菜花、絲瓜,就是有人收成多了拿出來分享,台北人聽來簡直不可思議。蔣勳說:「我來這邊也重新調整自己跟人的關係,忽然覺得好不一樣。」
人與土地的連結親密,食物就是自家田裡、院裡種的,不是商品,所以蔣勳驚喜發現,池上的枇杷連皮吃,因為自己種的沒農藥;而每一家的廚房可能都藏著寶,也許是40年的老菜脯、老橄欖、自己做的胭脂梅,那梅子可是人工採摘,絕不像外面都是落草劑一噴省事。
「我們這一代好幸福,經歷了台灣還沒有很工商業化的時代,所以有一些農村社區的記憶。」蔣勳說:「如果沒有這個記憶,就不會相信在池上還有這種傳統的鄰里關係。」
蔣勳說:「自然秩序和土地倫理,是都市裡愈來愈陌生的東西,我已經忘了。人在都市裡,真的會比較自閉、憂鬱,一旦身體跟大自然的秩序無法接在一起,那一定焦慮、也一定痛苦。」
蔣勳也算半個池上新移民:「我不只是一個駐村藝術家,其實是感覺到台灣一定會有一個新覺醒,會問自己為什麼一定要在都會裡跟人家打拚。其實好的生活就是健康的生活。」
「池上變成一個最好的榜樣,空氣好、水好、米好。」蔣勳認為,這三點足以吸引新移民,「如果這個地方只是老人的懷舊,沒有什麼意義,我覺得很明顯是年輕人進來了。」
他舉例,幾年前雲門來此演出「稻禾」,林懷民要求舞者體驗農村生活,安排他們去割稻,晚睡的舞者們乖乖早起下田,中午就坐在田壟上吃米苔目,對這些年輕人來說,那是一次土地的洗禮。
那一次帶著舞者割稻的葉太太,其實寫了一手好書法,蔣勳說:「這邊的人,都在學書法,就是耕讀的傳統吧。這邊真的臥虎藏龍。」
「到池上,我最大的領悟就是『天長地久』,根本不能急,農民把秧插在那裏,就是要等苗慢慢長大。」蔣勳說,像是沿著卑南溪慢慢走,溪水有它的速度,流到每一條池上的水圳中,灌溉每一片農田。
蔣勳說:「那就是唐詩說的,『水流心不競』,跟著溪水走,少掉了跟人家競爭的心。」尤其,看到婦女在藍天白雲下的溪澗洗衣,在池上,生活就是這麼簡單。

池上的「鬧區」不大,蔣勳這個異鄉人,走著走著,就成了當地人,東邊吃飯、西邊找茶,都成為街坊。
蔣勳大愛四神湯,到了「非吉本不吃」的程度,天天上門,遇到人家店休,還要提前來打包回家當存糧。吸引他的原因,無非是料好實在,四神到齊不偷料,該有的噴酒步驟也沒省略,一碗湯濁白濃郁,溫潤身心。
(089)865160
店內熱氣蒸騰,店員純手工做豆皮,庭院裡客人垂涎等著小火煎得略焦的豆包。蔣勳持筷直攻,邊吃邊讚:「好好吃喔,東西不複雜反而好。」
(089)862392
原是梁姓農家的穀倉,60年來陪伴當地人,經中原大學團隊改造成藝術館,從物質的糧食變成精神的糧食。蔣勳捐了自己在池上最重要的一件作品「池上旭日」。
(089)862089
蔣勳在發現池上有好吃又健康的食物後,自己就不太煮了,常常就到這裡用餐。選擇品項不像都會區那樣兩大排,但全是自然食物,可能就是店家自家種的。老闆娘的胭脂梅更是蔣勳心頭好。
(089)861733
女主人張力尤會送瓦斯,也會煮好吃的杏仁茶,變成蔣勳在池上時的安神飲品,吃完飯一定來一杯才回家睡覺,有時配上油條、有時叫一分「牛汶水」。
(089)865566
蔣勳進到書局,先玩起店貓來,兩隻貓兩個性格,他早就摸透,拿出紙筆就素描起來。
店面不大但理想夠大,認真地設置了作家專櫃,希望在這個小地方播下文化的種子。老闆簡博襄還是國內少有的管風琴調音家,對池上在地文化很用心。
(089)862046
滿屋子的手工皂材料與成品,開在偏離「鬧區」的地方,堅持費工費成本的天然手工製。蔣勳讚歎:「這裡人的生活還是有講究,他們不會要太隨便的東西。」
(089)861172
蔣勳站在自然光圍裹的畫室裡,拿著畫筆,試圖把風的流動引到已畫了一年多的大波池荷花油畫上。這是他在池上駐村以來的新感受。不久前,他也站在台北的藝廊裡,對著觀眾說明一組悉達多太子畫像的故事。
沒有界限、沒有框架、沒有包袱,人生邁入七十的蔣勳,像一條大河將注入大海,對自己隨心所欲,更多的寬容與平和。
「我想畫夏天大坡池的荷花,已經畫一年了,最近我想把風的感覺加進去,讓畫有一點動起來的感覺。」這是蔣勳在池上可以享有的奢侈,自然是最好的老師,「從早畫到晚,就會感受到一年四季、甚至晨昏之間的光在改變。」
自然的光和人為的光,在畫家眼中絕對不一樣,若加上了風的姿態,光影的變化非常漂亮,「你怎樣感覺到自然、你留在畫布上的東西,跟我在台北畫畫的感受很不一樣。」
蔣勳指出,印象派、巴比松畫派,莫內、米勒等畫家都跟農村發生關係、行走在自然中,梵谷還是在田野裡畫畫,但現在很多藝術家是窩在都會裡,「室內的經驗需不需要在適當的時候再一次打開門走出去?這是我在池上駐村很大的一個感受。」
蔣勳在池上,常常在田野裡走,也用了藝術家的眼光看這個地方。例如春分前後、清晨五點多的大坡池,完全像一張宋元的水墨畫;陽光出來後,色彩愈來愈飽和,紅的花、綠的草全部跳出來,就變成西洋的畫了,「這都和光有關,但在都市裡感覺不到。」

駐村經驗改變了蔣勳的繪畫觀念:「在池上是印象派,到八里畫人像,更多一點立體派、野獸派。」
這是來自於對比。他從難得遇到人但見面就會招呼的池上,坐普悠瑪號回台北,轉乘捷運回家,一路上就在觀察人,看年輕人戴著耳機滑手機、看各種路人不自覺的表情,這些都是他以前不會注意的,可是現在,蔣勳會用手機偷偷拍下來,再轉成畫作。
「我回到池上,就好像回到一個大自然當中,對話的對象可能是日出日落、星光、苦楝花、稻穀秧苗。回到台北,我就跟人對話,人裡面有很迷人的東西。」蔣勳說:「所以我的畫風就變成兩種了。」

蔣勳10月起到12月16日期間,從自己的各個藝術階段,抽樣整理出「天地有大美」個展,在台北谷公館舉行,除中國的山水畫外,幾幅脫自「維摩詰經」的人像畫,強烈而搶眼。
蔣勳認為,人要面對所有真實的欲望,要在人體的現實中去修行,一組三件的畫作,有人體的渴望、恐懼,居中一幅正是悉達多太子在修行,畫下一段文字,抄錄「維摩詰經」的「是身如焰」一段經文。
展覽中還有外界熟悉的蔣勳風格油畫、水墨、書法,有大山大海的長卷,也可以是身邊的小事,如一幅流浪狗油畫,就是蔣勳少有的動物畫,那是他在2010年心臟病出院後,每日在淡水河邊走一萬步時,認識的兩隻流浪狗。
這次展覽有如蔣勳的藝術整理,但在池上還有另一場小展覽,那將是他的「私藏」,有1968年的自畫像、有金剛經書法、有年少時速寫的卡繆等等偶像。這裡更像蔣勳回頭看年少的自己。
蔣勳從不諱言在擔任東海美術系的系主任那7、8年最為痛苦,被行政與會議困住的他,羨慕著能躺在東海教堂下曬太陽、讀楊喚詩集的年輕人。
蔣勳掙脫,到了巴黎,在馬廄裡瘋狂畫畫,體會了海明威說的「如果二十幾歲在巴黎,巴黎就一輩子跟著你」;又回到八里,面對著淡水河潮起潮落,然後到池上。
蔣勳說:「2014年我來到池上,又經過心臟發病,裝了支架,我的身體開始進入一個比較老年的階段,要怎樣去告別青春?一生其實很像一條河流,就是激流險灘、中流的洶湧浩大,到河口時應該比較寬闊、比較寬容跟平靜。」
而池上真的帶給他安定的力量,在這個最適合的年紀。蔣勳說,再年輕一點的自己,也許住不了池上,但此時的他已懂得包容,理解年輕人會像希臘羅馬神話裡的伊卡魯斯一樣想飛出去,「我希望在某個衰老的年紀,看到年輕人走過,會有一種祝福,願他可以好好活出自己。」

展覽的畫作角落,有些印著「花甲」、有些是「從心所欲」,那是蔣勳請一位學生金工鑄造的印,「六十年一甲子,一個人大概已經經歷生命裡面該經歷的事。今年我七十,論語講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,但我不要不逾矩,我想打破規矩。」
「從心所欲是個很大的嚮往。」蔣勳說:「接下來想做的事,就好好畫畫吧。」他一直是多元創作,寫詩、小說、書法、會畫,但現在想把文字慢慢轉成圖像,因為到了文字思維比較辛苦、記憶力下滑的年齡,「這個年齡畫畫很快樂,有身體上的運動,跟空白畫紙的關係比較直覺。」
「這個從心所欲,反而是隨著年齡釋放出來,就希望慢慢多畫一點、少寫一點。」蔣勳說,最好是「兩袖清風」,那就是自由。
